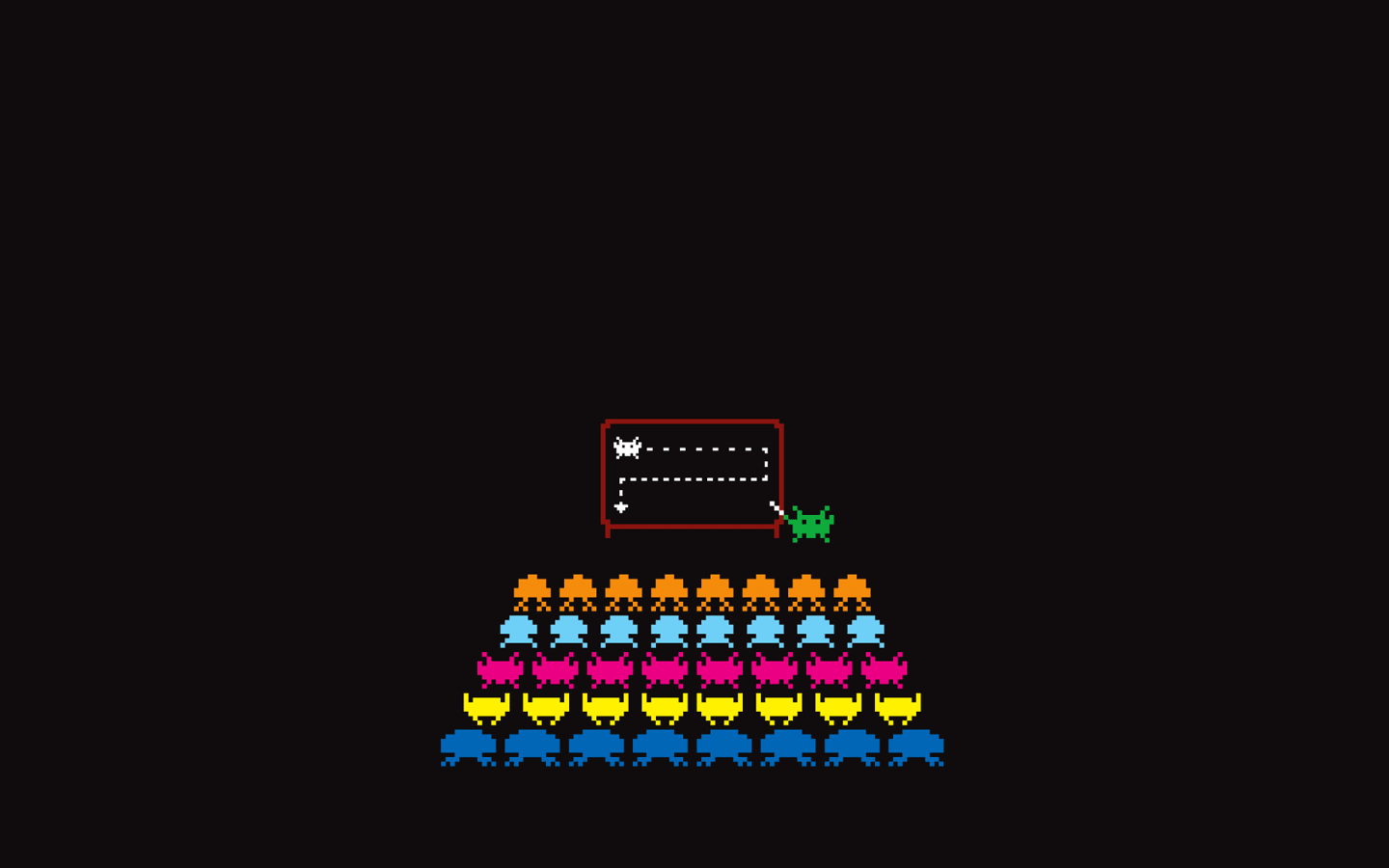正见——佛陀的证悟(三)诸法无我 (选摘)
所有这些不同的情绪及其结果,都来自于错误的理解,而这个误解来自一个源头,也就是所有无明的根源—-执着于自我。
自我只是另一个误解。当我们看着自己的身体(色)、感受(受)、想法(想)、行为(行)和意识(识)的时候,我们通常制造出一种自我的概念。人们受制约,把这种概念视为恒常而且真实的。
但是悉达多了悟到,不论是在身体里或外,都找不到一个独立存在的实体,足以被称为自我。如同火圈的视觉错幻一般,自我也是虚幻的。它是谬误的;基本上错误,而究竟上不存在。但是如同我们被火圈所迷惑一般,我们也全都被自我所迷惑了,执着于谬误的自我,是无明的荒谬行为。它不断地制造更多的无明,导致了各种痛苦和失望。
无明单纯的就是不了解事实,或对事实了解不正确,或认识得不完整。所有这些形式的无明,都导致误解和误判,高估和低估。假设你正在寻找一个朋友,忽然看到他在远方的田野中。一走近,却发现你误把一个稻草人当做是他了。你一定会感到失望。这并非有个恶作剧的稻草人或你的朋友试图偷偷摸摸误导你,而是你自己的无明背叛了你。任何源自无明所做的行为,都是冒险。我们在不了解或不完全了解的情况下行动,就不会有信心。我们根本的不安全感因此而生起。创造出所有这些有名或无名、已知或未知的各种情绪。
悉达多了悟到自我并非独立存在、自我只不过是一个标签、因而执着于自我就是无明,这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发现。然而,虽然自我这个标签或许毫无根据,要摧毁它却不是一个简单的任务。执着于这个称作自我的标签,是所有的概念中最难以破除的。
魔罗只不过是悉达多的我执。故事中,描述魔罗是个英俊威武、无役不克的战士,这个比喻相当适切。自我,如同魔罗一般,威力强大且贪得无厌、自我中心且虚伪欺诈、贪求众人目光、机敏伶俐且爱慕虚荣。我们很难记住,自我如同火圈的幻相一般,是和合而成、不独立存在而且善于改变。
骄慢和自怜息息相关。我执纯粹是一种自我纵容,认为自己的生命比其他人的都更艰难更悲哀。当自我发展出自怜的时候,便让其它人生起悲悯的空间消失了。
虽然我们不认为自己这么绝望,而且相信自己是受过教育、正常、清醒的,但是当我们看见及感受一切都是真实存在时,我们的行为就如同那位沙漠中的迷失者。我们急切地想要找到真实的伴侣关系、安全感、表扬、成功,或只是安详宁静。我们甚至能抓到与欲望相似的东西。但就象那位迷失者,当我们依赖外在的实体性时,终究会失望。事物并不如其所显现—–它们是无常的,而且不完全在我们的掌控之中。
如果我们象悉达多一样确实地去分析,就会发现诸如形体、时间、空间、方向、大小等附加的标签,都很容易被解构。悉达多了悟到,甚至自我都只存在于相对的层次,恰如海市蜃楼一般。他的体悟,终止了期待、失望与痛苦的循环。在证悟的时刻,他自忖,我已找到了一条深奥、安详、非极端、清晰、满愿又有如甘露一般之道。然而,如果我想表达它,如果我想教给他人,没有人有能力听闻了解。因此我将留在林中,安住于此祥和状态之中。
然而,悉达多并非不理性,他只是明确地指出一般的、理性的思惟是有限的。我们不能,或不愿超越我们自己的舒适区去了解。用昨日、今日、明日这种线性的概念来操作,比如说“时间是相对的”,来得实用得多。我们没有被设定成这么想的:我能不改变大小或形状而进入那牦牛角。我们不能破除大和小的概念;相反的,我们一直被世代传下来的安全而狭隘的观点所局限。然而,当这些观点被审视时,却都站不住脚。举例来说,这个世界如此依赖的线性时间观念,无法说明时间没有真正的起始也没有终止的事实。
因此当我们听到一个人不改变尺寸,就可容入牦牛角中时,我们没有太多选择—–我们可以很“理性”,认为这根本不可能而驳斥它;或者我们引用某种对法术的神秘信仰或盲目崇拜而说,当然,密勒日巴是多么伟大的瑜珈行者,当然他能这么做,甚至还不只是这些呢。这两种见解都是扭曲的,因为否认是一种低估,而盲信则是一种高估。
一条河,水在流,永远在变,然而我们仍然称它为河流。如果一年之后我们再度造访,会认为它是同一条河。但它是如何相同的呢?如果我们单独挑出一个面向或特性,这相同性就不成立了。水不同了,地球在银河中转动的位置也不同了,树叶已落,新叶又长出来了—-剩下的只是一个相似于我们上次见到的河流表象而已。以“表象”作为“真实”的基础是相当不可靠的。经由简单的分析,就能显示出我们一般对所谓真实的基础,都只是一些模糊的概括和假设。虽然悉达多也使用一般人定义“真实”时所用的字眼—-非想象的、确定的、不改变的、无条件的—-但他更精确地使用这些字眼,而非概括性的。在他的观点上,不改变必然意指在所有的方面都不改变,甚至经过彻底的分析后,仍然绝无例外。
悉达多发现,要确定某个东西真实存在的唯一办法,就是证明它独立存在,而且不需要诠释、不能造作或不会改变。对悉达多而言,我们日常生活上一切似乎能作用的机制,不论是身体的、情感的及概念的,都是由不稳固、不恒常的部分所聚合而成,因此它们随时都在改变。我们可以在惯常的世界中了解这个论点。举例来说,你可以说你在镜中反射的影像不是真实存在的,因为他需要依赖你站在镜子前面才行。类似的,事物要真实或独立地存在,就不能被制作或被创造的,因为这要依赖制造者。
许多对佛陀的教法不甚了解的人,认为佛教是病态的,他们认为佛教徒否定快乐,只想到痛苦。他们设想佛教徒排斥美丽及身体的享受,因为这些是诱惑;佛教徒应该是纯净而节制的。事实上,在悉达多的教法中,并不特别反对美丽和享乐甚于其它的任何概念--只要我们不认为它们是真实存在的,而迷失其中。
虽然悉达多证悟了空性,但空性并不是由他或任何人所制造的。空性不是悉达多获得天启的结果,也不是为了让人们快乐所发展出来的理论。不论悉达多开示与否,空性即是如此。我们甚至不能说它一直都是如此,因为它超越时间,而且不具形式。空性也不应被解释为存在的否定(也就是说,我们不能说这个相对的世界不存在),因为要否定某个事物,你就要先承认有某个东西可以被否定才行。空性也不会消除我们日常的经验。悉达多从来没说过有什么可以取代我们所觉受的更壮丽、更美好、更纯粹或更神圣的东西。他也不是虚无主义者,否定世间存在事物的显现与功能。
悉达多会同意这两种情况--当你醒着时,你不能飞;而当你睡着时,你能飞。这道理是在于因缘是否具足;要能飞翔的一个缘,是睡眠。当你没有它,你就不能飞,有了它,你就能飞。假设你梦见你能飞,而醒来后还继续相信你能飞,那就麻烦了。你会掉下来,而且会失望。悉达多说,即使在相对世界中醒着,我们还是在无明中沉睡,如同在他出走那夜的宫女一般。恰当的因缘聚合时,任何事情都可能出现。但当因缘消散,显现也就停止。
这也是为何在悉达多教法一千五百年后,一位叫帝洛巴的佛法继承者,对他的学生那洛巴说,不是显现(外相)困住了你,而是你对显现(外相)的执着困住了你。
如同环球小姐选美一样,在这个世界上,我们所做、所想的任何事物,都有是基于一个非常有限的共同逻辑系统。我们非常强调共识。如果大多数人同意某件事物是真实的,通常它就变成正当有效的。当我们看着一个小池塘,我们人类认为它只是个池塘,但对池里的鱼儿来说,这是它们的宇宙。如果我们采取民主的立场,那么水中族群一定会赢,历为它们比我们这些观池塘者为数多得多。多数决不见得永远都对。糟糕的大卖座影片可以赚得大量的利润,而一部独立制作的优秀影片却只有少数人观赏。而且由于我们依赖群体思考,这世界通常是被最短视而腐败的统治者所治理;民主制度只是诉诸于最小公约数而已。
然而了悟不必是致命的。我们不需要象井蛙一般,面对空性惊吓而亡。如果海蛙能够有稍微多点的慈悲心和善巧,也许它可以做一个更好的向导,井蛙也不至于吓死,也许它还会移居到海边也说不定。而我们也不需要有超自然的天赋才能了解空性。这和教育以及愿意观察事物所有的部分以及隐藏的因缘有关。有了这种洞见,我们就会象布景设计师或摄影助理在看电影。专业者能看见我们所看不见的东西。他们看见摄影机如何布置,以及其他观众们不知道的电影技巧,因此对他们而言,这幻相被拆解了。但专业者在看电影的时候,还是可以尽情享受。这就是悉达多超然的幽默。
悉达多没有一开始就用空性来惊吓大家,反而以一般的方式,诸如禅定以及行为规范--做正确的事、勿盗窃、勿妄言等来教导众多的弟子。根据弟子的本性,他定下了不同程度的出离及苦行,从削发到不食肉等等。对一开始无法听闻或了解空性的人,以及天性适合苦修的人而言,这些状似宗教性的严格道路很有效。
业(Karma)这个字几乎和佛教成了同义字。通常它被理解为一种道德系统的报应—-恶业与善业。然而,业只是一种因果的法则,不应该与道德或伦理混淆。
你也行会认为这是矛盾的。佛陀自我矛盾,说他不存在,一切皆是空性,然后他又教导了道德和救赎。然而这些方法是必要的,以免吓走那些尚未准备好,还不能被引介空性的人。他们用了这些方法,因而变得祥和,易于接受真正的教法,这就如同说那里是有一条蛇。然后把领带丢到窗外一般。这些无限的方法就是道路。然而,道路本身终究也需要被抛弃,如同你抵达彼岸时,就得抛弃舟一般。你抵达时必须要下船。在完全证悟的那一刻,你必须抛弃佛教。精神之路是一个暂时解答,它是在空性被了悟之前所使用的安慰剂。
如同在电影院里的孩童,我们被幻相掳获了。从这儿开始,衍生了我们的虚荣、野心和不安全感。我们爱上了自己创造的幻相,发展出对自己的外表、财富和成就过度的骄慢。好比戴了面具,却骄傲地认为面具是真实的你。
了悟空性的悉达多,对菩提树下的忘忧草或宫殿里的丝绸坐垫没有好恶分别。金线织成的坐垫价值较高,完全是由人类的野心和欲望造作而来的。事实上,山中的隐士也许会觉得忘忧草比较柔软而干净,而且最大的好外是坐坏了也不需要担心。你不需要对它喷药,以免猫用爪子去抓它。宫廷生活充满了这类的“珍品”,需要相当多的维修保养。悉达多是属于比较喜欢草垫的人,因此他不需要常常回家去补充什么东西。
我们人类认为心胸宽广是一种美德。要扩展心胸,重要的是不要安于令我们舒适或习惯的东西。如果我们有勇气超越世俗,不被惯常逻辑的界线所限制,就能得到利益。如果我们能超越界线,就能了解空性是如此可笑地单纯。密勒日巴躲进牦牛角不会比某个人戴上手套还令你讶异。我们所要挑战的,是对惯常逻辑、文法、字母、数学公式的执着。如果能记得这些习惯的和合本性,我们就能断除它们。它们不是不能破除的,所需要的只是一个条件完全正确、资讯适时到位的情况,你可能突然发现所有依赖的工具都不是那么坚实,它们有弹性、可弯曲。你的观点会改变。